黄大荣(山东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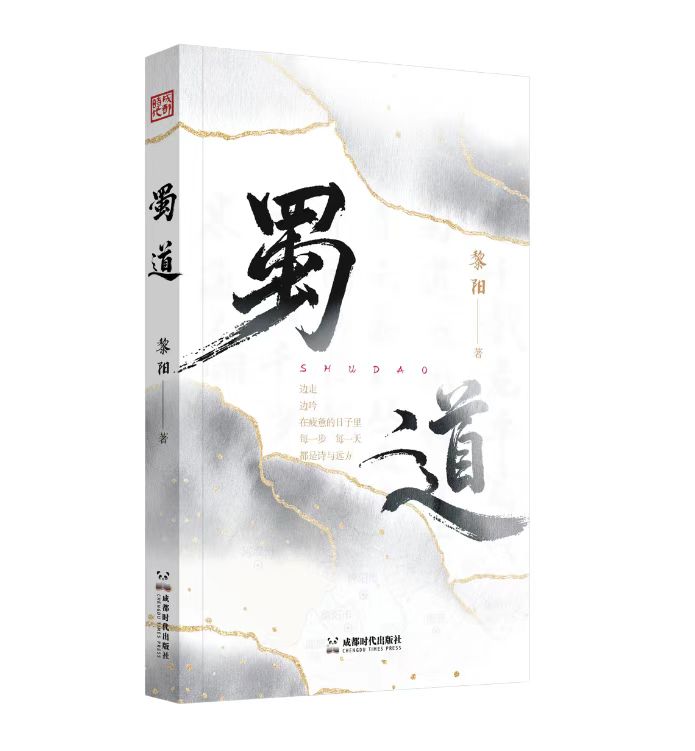
作为《星星诗刊》的一名作者和读者,诗人黎阳是《星星诗刊》的编辑,虽然我与诗人黎阳从未谋面,我对诗人黎阳的了解,只能停留在他发表在各大报刊杂志的文章和在《星星诗刊》作者群及他的微信空间里的文学作品。在拜读完诗人黎阳近来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又一部诗集《蜀道》之后,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,全算班门弄斧。
在当代诗歌的版图中,地域文化一直是重要的创作源泉,无数诗人从脚下的土壤汲取灵感,以笔为凿,雕刻出一首首蕴含风土人情与历史底蕴的诗篇。诗人黎阳的新诗集《蜀道》便是这股地域创作浪潮中机具特色的一朵浪花,它不仅为四川地域文化的诗歌表达开辟了新路径,也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思考纬度。
黎阳的诗集《蜀道》以其独特的结构设计和文化解码方式,构建了一部穿越时空的诗歌版“四川志”。这部诗集以四川21个地市州的车牌字母(如川A、川B)为章节名,将现代交通符号转化为地域文化坐标,通过“川A成都”“川T雅安”“川E泸州”等章节,串联起从地理、历史到人文的多维观察。这种创新的结构设计不仅打破了传统地域写作的框架,更以“公路片”式的叙事,让每个章节既是独立景观,又通过诗人的行走连成精神版图。
一、地理坐标与文化基因的深度融合
在“川A成都”中,诗人以“在砖瓦的缝隙里,寻觅光阴的碎片”解构城市记忆,将东郊记忆的工业遗迹转化为时光的容器。这种书写超越了表面的城市景观描绘,而是通过“砖瓦缝隙”这一意象,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叠合。而“川T雅安”以“心在草木九宫间”呼应茶马古道的历史回响,将茶文化与地理脉络交织,使草木成为文明的载体。在“川E泸州”,“玉碗盛来琥珀光”解构了酒城的文化基因,将传统酒文化转化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诗性体验。
诗集中的地理书写并非简单的地域标识,而是深入挖掘每个地区的文化密码。例如“川U阿坝”章节中,“飘下雪山的红旗”与羌族刺绣的“云云鞋”形成时空对话,将红色历史与民族文化并置;“川V甘孜”捕捉“一只雪豹从都市里捎来春天的温暖”,在现代性震颤中展现自然与城市的张力。这种全景式扫描,使诗集成为一部“诗歌人类学”田野报告,既有宏观的文化俯瞰,又有微观的生活切片。
二、历史纵深与现代性思考的双向互文
作为东北籍“蓉漂”诗人,黎阳在川十五年的生活体验成为创作底色。早期作品《成都语汇:步行者的素写》和《西岭笔录》带着异乡人的猎奇,而《蜀道》则是深度观察后的思考。诗人通过“见今思古”的手法,打通了古往今来的时空界限。例如在“川H广元墨痕”中,他写蜿蜒的古道和“尺八缝隙里听唐朝的吟诵声”,将摩崖石刻的模糊字迹转化为戍边将士的乡愁载体。这种历史书写并非简单的怀古,而是将历史隐喻融入当代生活,如都江堰的水被视为“蜀人应对无常的历史隐喻”。
诗集同时触及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。南开大学罗振亚教授指出,黎阳的写作超越了地域文学常见的风情展示,触及了身份焦虑。例如在“川V甘孜”中,雪豹与都市的并置,暗示了自然生态与现代文明的冲突;而车牌作为“现代社会的地理图腾”,既标记方位,也暗示着地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坐标重构。这种双重书写使《蜀道》既有历史的厚重感,又具备现代性的锐度。
三、新古典主义美学的当代实践
黎阳的诗歌被评价为新古典主义,其特点在于对古典意象的现代转喻。他多次直接引用唐诗宋词名句作为诗题,如“白云深处有人家”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,但并非简单复制,而是融合现场观察形成“古典新义”。例如在“川A成都”中,“砖瓦的缝隙”与杜甫草堂的意象形成互文,将古典的“诗圣”精神转化为现代城市的生存哲学。
诗人注重语言的音乐性与画面感。他弱化叙事,强化抒情,通过舒缓的节奏和反复的意象(如“远方”“光芒”)营造出悠扬的韵律。例如“还在远方/或许远方的远方”的句式,既延续了古典诗歌的复沓之美,又注入了现代的漂泊感。这种美学追求在“川T雅安”中体现为“心在草木九宫间”的凝练,将茶的氤氲之气转化为视觉与听觉的通感体验。
四、地域写作的范式突破与文化担当
《蜀道》的出版被四川省作协列入“四川当代文学文献档案库”,并计划开展全国“诗歌行走”活动,其意义不仅在于文学创作,更在于文化传播。成都时代出版社总编辑王晋升认为,诗集以车牌为章节名,既助力四川文旅,也让读者从诗中寻找故乡。这种“以诗为媒”的实践,将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推广结合,为当代诗歌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新范式。
诗人黎阳在首发式上表示,希望通过《蜀道》让更多人感受到四川的底蕴,这不仅是地域赞美,更是对生命和自然的礼赞。这种创作理念使诗集超越了个人抒情,成为文化自信的表达。正如龚学敏所言,黎阳的蜀道是“从爱情出发的诗人之路”,他将个人经历与四川文化深度融合,最终形成更宽广的精神版图。这种从“异乡人”到“在地者”的视角转换,使《蜀道》成为当代地域写作的典范。
《蜀道》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一部地理志、文化史,也是一部精神自传。黎阳以车牌为线,编织出四川的诗意地图;以历史为镜,映照出当代人的文化身份;以古典为基,构建起现代诗歌的美学范式。这部诗集不仅为四川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,更为当代诗歌的地域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。正如杨献平评价的,《蜀道》“既带有极强的历史纵深,又紧密联系当下时代,具有很强的文学宽度和厚度”,它让我们看到,诗歌不仅可以是个人的抒情载体,更能成为地域文化的解码密钥和时代精神的镜像。
